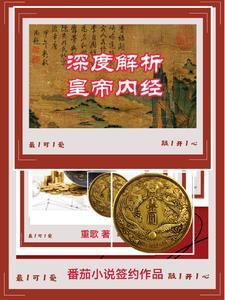泉州小说网>[西方名著衍生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薄莉以为埃里克会让他们滚。
谁知下一刻,他突然抛出?绳索,一把套住那小混混的脖颈。
——这不是荒郊野岭,而是城里。
薄莉连忙抓住他的手臂。
他手臂的肌肉已?绷得像石头一样硬。
如?果?不是薄莉按住他,让他顿了一下,恐怕那小混混已?身首异处。
“亲爱的,这里是城市!”她凑过去,压低声音,“忍忍吧,反正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
她对他的称呼,差点让他一个手抖直接勒死面前的小混混。
埃里克停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收回绳索。
那几个流氓无赖忙不迭地跑了。
埃里克没有说?话,一扯缰绳,似乎也要离开?。
薄莉骑马跟了上去。
走出?贫民街区,他才微微侧头看?向她,冷声说?:“跟着我干什么。”
“我听说?……”薄莉催马走到他的身边,“米特中邪了。”
“所以?”
“是你?干的吗?”她问。
他的语气很冷很冲:“与你?无关。”
自从他发?现?自己想要吻她,整个人就被一种暴怒似的冲动席卷了。
他从来不是冲动易怒的人。
可能因为年岁渐长,他开?始频繁做梦,梦见她的呼吸,她的体温,她濡湿鲜红的口舌。
但?每次醒来,他都能将那种冲动强压下去。
最近,似乎压抑不住了。
——她无论做什么,都会让他的胸腔掠过无法解释的震颤。
那种震颤,会让他突然生出?一种粗暴的冲动。
想要扣住她的脖颈,咬伤她的皮肤,用力抱住她,直到骨骼发?出?被挤压的声响。
她跟米特幽会的那天,他只觉得头脑微微眩晕,差点就被这冲动控制了。
惩罚完米特,他闭上眼睛,仍然能感到血管里暴怒的震颤。
他在郊外租了一幢公寓,四周没有邻居,内部?家具极为简单,除了日常所需,只有一架三角钢琴。
他听见自己呼吸粗重,试图用音乐宣泄出?这冲动。
然而不行,血里的燥热似乎融入了乐曲里,连音乐都变得凌乱疯狂起来,如?同疾风骤雨,每一个音符都变得尖锐至极,蕴藏着恐怖的爆发?力。
只听一声锐响。
他触键的力道?太过猛烈,琴弦断裂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内心?才稍稍冷静下来。
但?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他感到无法形容的罪恶感与羞耻感。
血已?冷却,只剩下一手黏凉。
像玷污或打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