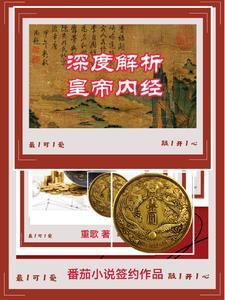泉州小说网>天歌行 走进修仙 > 第八十章 罪首(第1页)
第八十章 罪首(第1页)
次日天晴,日朗风清,方宁睡了一个极安稳的觉,日光落在檀香缭绕的山头,将一切的坏事皆抛诸脑后。
“此时下山,加快脚步的话,今日我们应能抵达昌宇码头。常威借给我们的手下刚好一十七人,加上我们,伪装成运送队的模样,运送铜矿,说不定能让我们直捣长龙,一举拿下魏督监背后之人。”方宁收拾完包裹,与沈昱邵夫子离开青檀寺,山道路窄,三人一前一后地跟着,马蹄轻快,乘风而去。
沈昱跟在方宁身后,沉肃道:“若真有如此简单,也算万幸。我就怕前路艰难,没等我们发现罪证,运送队的真貌就被发现了。师妹,你这一路过于胆大,切记藏锋。”
方宁挑眉回头,见沈昱长发高束,一根莹白玉簪盘住,露出利落分明的五官,感叹道:“许久未见师兄真貌,都快忘了我师兄貌若潘安,神采动人。”
沈昱马背不稳,额前青筋直跳,预感不好,“你有事说事。又来这套。”
方宁嘴角笑意未达眼底,紧了紧马绳,放慢脚步,与沈昱的马并肩而行,狠拍沈昱马背,看着沈昱的马急驰而去,而沈昱如摇晃的稻草人一般,在风中凌乱破碎。
她饶有兴致地晃动着手腕,“如此扫兴,将来谁敢当你媳妇。恐怕是新婚之夜,还得听你说大道理。”
有了方宁的助力,沈昱等人比预料的更早一刻抵达昌宇码头。
申时刚过,落日余晖照映在湖面上,粼粼水光把这本萧条沉寂的码头照出一分暖意来。
方宁领着朝常威借来的人马,颇有气势地朝着码头边,唯一停靠船只的船夫道:”老人家,我们要运东西去对岸,敢问多少银子一箱货?”
那船夫的头发已经银白,胡须是被打理过后的精致,藏在帽笠下的狭长眼睛落在方宁身后时,幽幽一转,“申时落货,要付双倍的价格。”
方宁操着一口榕城口音,在船夫耳边轻声道:“江上春常早,闽中客去稀。老人家,我们主子说了,您与他都是榕城的,价格可好商量些?”
方宁临走前,特意去翻过领队遗物,找到与那船夫胡斐的笔迹,二人因都是榕城本地,便以此暗号相约。
果然,胡斐听见这句诗,脱下帽笠认真瞧了眼方宁的箱子,压低声音道:“他怎就派你一个女流之辈来了?”
方宁皱眉不悦,反问道:“主子的心思,岂容你一个老匹夫猜忌?我是女子,扮作商队,掩人耳目,不可吗?”
胡斐见方宁咄咄逼人,心里的怀疑却消散几分。
他查阅了一遍矿藏,并无错处,才安心道:“既是如此,姑娘请回吧。这些箱子我会按时送达的。”
方宁显然没想过还有这一茬,水路一程,竟不由他们运送。
很快,她将原本铜矿的箱子锁心一一检查,复扣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道:“那便有劳操心了。”
沈昱跟在队伍最后,见方宁走得极潇洒,便知她有后招。
果然,方宁等带着运输队走没了影,择了离码头最近的茶楼坐下,远眺江面,见胡斐已将货物一一运载,往西边渡。
“你准备何时跟上?”沈昱皱眉,见原本还硕大如巨蛇卧江的船,已经远渡到如他们茶盏中的浮叶时,终是按捺不住。
方宁与邵夫子倒是不急,一个品茗,一个饮酒。
方宁调侃道:“师叔,你也少喝些。若他日手抖脑笨,再做不出能追踪千里的香来,可如何是好啊。要不把你这好手艺,全部传给我如何?”
邵夫子一早看出方宁在检查货物时,将追踪香塞入每一个箱子的铜扣里,讪讪一笑,“你个没大没小的。想要我的手艺,先学会乖顺些。”
方宁别了别嘴,暗道一句不稀罕,算着时辰也差不多了,掸走手上茶点的碎屑,“那我们便启程吧。”
他们一路随行,保持着三里距离,以防被胡斐发现,直到船停靠在一座荒山边的水道上。
方宁瞧着手里的地图,此山未经开凿,本应人迹罕至,但山道另一旁,已有炊烟袅袅,一看就是有人居住的模样。
他们跟着运送铜矿的船夫身后,随着他们进入一条窄小暗道,只能堪堪容纳一人的身量,沈昱与邵夫子都得弯腰低行,一看就是匆忙开凿出来的。
方宁不知跟着那群运送队的人,弯弯绕绕走了几许,终于通见日光时,却瞧见一座偌大空阁,横向一里,纵达三丈,门前有一支队伍在巡逻。
他们择了个视线盲区的山壁逗留,瞧着那座空阁,依旧让人不敢相信。
一个连山道都没有的荒山上,竟造出如此巨大的亭台楼阁,里面究竟又干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勾当?
方宁见胡斐已通过门前把守人员验证,算着门前门卫多久调换一次,与沈昱商量道:“门前队伍两个时辰会调一批人重新把守,侧门有片刻的空档,可以让人潜进去。我先一个人进去,若一炷香时间里,我没回来,就劳烦师叔与师兄出马了。”
沈昱对方宁独身前往,多有担心,“你一切小心。危急存亡之际,便供出我的位置,以一换一。我若死了,陛下必不会善罢甘休,里面的人自然会忌惮一些,不敢轻易伤你。”
方宁鼻尖稍酸,只觉山风真是吹得刁钻,安慰道:“师兄放心,不会有事的。何况师妹我觉得你在陛下心中,也没有如此重要,自然会多加小心。”
说罢,她见门卫有调换之意,没等沈昱反驳,道了句珍重,很快攀上山壁垂坠的枝桠,如暮雀烟波,消融于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