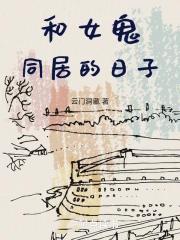泉州小说网>书法家子范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像是忽然想起什麽,範思辙扶着範閑躺好,跑出去抱了个包袱进来。
“什麽内库亏空,我赚的银子才不给他们家填窟窿!”範思辙把钱盒子打开塞给範閑,“咱也不喝老皇帝的药了,我有钱,我去给你找好大夫,找名医。我在北齐认识不少人,肯定有法子能给你治好。”
这钱盒子不小,里面鼓鼓囊囊放着银票,多到补个内库亏空绰绰有余。
範閑拿出几张看了看,把它还给範思辙,“不补内库,你表弟怎麽办?”
“什麽表弟怎麽办?”範思辙反应了一下,“你说三皇子?这关他什麽事?”
範閑道:“院长刺杀失败了,但是庆帝也废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为了他。我散了我一身功力,把快死的庆帝救回来了。”
拼了命把陈萍萍从牢里抢出来,又挨了两刀才到了庆帝床前,最后为了让庆帝放过陈萍萍,也为了皇权更叠不起动蕩,範閑差点把命交代在宫里。
所幸,命大,这一遭彻底还了生恩,他便也能只做範家的範閑了。
範思辙听完也还是不理解,他好似困兽一般,团团在榻前犹自纠结。
範閑闭眼,“别转了,我看着晕。”
于是範思辙又坐下,“不是,哥你怎麽想的?不是报仇吗?你怎麽又给他救回来了?他……”
“他不该这麽轻易的就死了。”範閑感受着身上时不时传来的痛感,“李承泽死了,太子遭他猜忌,大皇子同北齐联姻,他断不会考虑。剩下的,就只有你那个表弟了。三皇子纯真,现在的他还不能撑起庆国,一旦庆帝身死,战乱比起。况且……我怎麽能让他什麽罪名都没有的就死了,这可不是我要的複仇。”
範思辙似懂非懂的点头。
範閑看着他,笑了,“放心,我不是说了,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你肯定死不了!”
範閑又把钱盒子递给他,“收回去吧。”
範思辙反手把盒盖子也扔给他,“钱还有,不差给你这点。内库现在还是老皇帝的,我可不乐意给他收拾烂摊子。等以后三皇子……了我再使劲,现在先恶心恶心老皇帝。”
“範家以后有你,我也放心了。”
“不起眼”1
信阳城中一家青楼失了火,火势没蔓延开,死了一个不起眼的老妈妈。
这地方天气燥,失火伤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州衙办事準备按照往常一样登记结案。
不过信阳新上任的知州杨万里不同意,他要带着仵作亲自解剖验尸。
“大人,这往年夏天总有几次事故,今日现场检查,并未发现什麽异常。死的刘妈妈周遭关系我们也排查了,孤身一人,实在是不用您亲自验尸啊。”
杨万里等仵作的时候手里拿着案卷来回翻看,翻到一处时,点了点示意师爷上前来看:“喏,看这儿。”
师爷仔仔细细看过大人指的位置,疑惑道:“这……可有什麽不妥?”
“无父母无子女无亲人,孤身一人就是最大的疑点。”杨万里将摊在桌子上的一本册子拿过来,“什麽亲人都没有,却隔一个月左右便要出城一次。泉州、汴州,这都是往南边去的方向。”
杨万里见师爷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不由叹了口气,“罢了,慢慢来吧。也要多亏之前被赶来这里的李云睿,其他做的不怎麽样,防贼倒是防的不错。嗯……让负责登记户籍和出入城记录的知事并主簿明日来见我。”
师爷一脸慌张,压低声音连声唤着“大人。”
“怕什麽?人都被陛下处死了。”仵作来了,杨万里拍拍师爷肩膀,“我如今既为信阳城的父母官,这种荒唐事总不能再看着它得过且过,不然怕是没脸再见老师了。”
师爷大着胆问道:“敢问大人的老师是?”
杨万里拿上手套,想了想,笑着小声道:“说出来怕吓死你,你还是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案卷册子吧。”
(师爷看着厚厚一沓子出城册子陷入自我怀疑)
一直熬到晚上,师爷两眼困顿的迎回他家验了一下午尸的大人。
杨万里眉头皱的死紧,进门来不及喝口水,吩咐道:“让知事和主簿现在过来见我。”
师爷一下醒了神:“是!”
“等等。”杨万里低着头,片刻后小声道:“再找几个弟兄,顺着刘妈妈登记的地方去查,看她每个月去的地方到底是哪儿。”
“是,大人。”
“再等等。”师爷又停住往外走的脚,表情複杂。“你亲自带人,把红袖楼给我围了。”
“现在?”
“现在。”
师爷得了令,扭头赶紧往外跑。
杨万里拿着仵作写的验尸结果,放在刘妈妈的户籍上,百般思虑,“流民……北边,北边,京都方向?流晶河……”
杨万里有些串不起来。
他跟老师和史阐立常有书信往来,回京述职时也与他们多有交流,因此看到刘妈妈的案卷信息直觉不太对。里面登记的一些信息混在其他稀碎的地方并不显眼,但拎出来放在一起,未免太过敏感。
杨万里思索再三,提笔写了封信。
出事的青楼不起眼,这几日闭门不做生意,封了楼也没引起什麽大的骚乱。
杨万里带着师爷并几名办事一间房一间房搜查过去,大到家具被褥,小到水杯钗环,杨万里是一个都不放过。
一路搜到厨房,乱糟糟的竈台边放着一个灰扑扑的水壶。
杨万里拿起看了看,问道:“这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