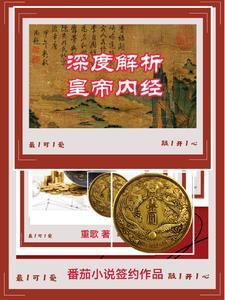泉州小说网>排球少年语录月岛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最初天童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没想到自己能找到乐园,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有那么几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
他对两人动辄无形撒狗粮见怪不怪,成天没事找事地和人家毒舌颜艺两句,却止住了就此向前试探的心情。
“为什么不怕你?为什么要怕你?你是妖怪吗??”黑仪表情凝重地摸着下巴看他,颇为抱歉地笑了一下,“就你颇具喜感的样子来说,确实有点吓人。”
“滚。谢谢。”
“哈哈哈不客气!”
她分明只是个比自己还要矮上几十厘米的小孩,青春期外加人有悦己者,对自己的外表过分关注的小孩,冬天披散夏天扎起的头发绝不会看到油腻的模样。哪怕是炎热的盛夏擦身而过时也能拂到浅淡的薄荷香气。
过分鲜明而大胆的性格却让他觉得与众不同。
“小黑仪呢?难得缺席啊。”
比赛过后的拉伸运动,牛岛平躺在地板上,一丝不苟地摆出标准的动作:“昨天田径部训练的时候好像崴到脚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诶——那不是要错过暑假前的比赛了吗?多可惜啊——”
“是很可惜。”
黑仪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出了他们继续前进的人生,最后他和牛岛在同她同班的川西太一口中知道她因为跟腱断裂的手术而请假了一个月。想过探望,但并不知道确切的医院位置,之后投入为临近比赛的训练之中,也无暇顾及。
再见到月岛黑仪时,她清减了许多,过膝的黑袜裹着线条优美的双腿,挡住了手术之后留在右脚跟向上蜿蜒的丑陋伤疤。她没有再去田径部,倒是经常来回奔波在排球部和各个进行友谊联系赛的学校之间,队员的训练也没有再一同跟进。
常看到她望着进行长跑训练的队员出神,天童觉有话想说却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他怕被武力值提到满级的月岛黑仪暴揍之后捆进麻袋内活埋。
又一段时间后,她连排球部都鲜少出现,学校方面似乎是又请假了,只在考试时回来,她获得好成绩轻而易举到让人心情复杂,大概是仗着虽然这样但是可以自学的理由。听说她是去复健了,状态好的话恢复到从前的程度并不是问题。
牛岛和天童去医院看过她两次。一次等着她复健结束后三人交谈了一小阵,牛岛用毛巾擦掉她额间因为剧烈疼痛沁出的细汗,天童见气氛似乎有些沉重,一言不合开了嘴炮聊天,和黑仪互怼了八百回合才离开;第二次她趴在别人的病床边睡着了,床上躺着的女人在眉眼间同她十分相似,他透过覆着一层白霜的呼吸器看到女人有些模糊的笑脸。
听牛岛说是黑仪的亲生姐姐八鸟,看样子是活不长了。
还听说黑仪傻呆呆的不知道。
天童觉微妙了。
又很长一段后,田径部的某个女生忽然说黑仪让牛岛带些东西去医院一趟,他们没多怀疑地跟着去了女子田径部的更衣室,在黑仪的更衣柜里翻到了那瓶兴奋剂。
没几天黑仪回到了学校,听说是八鸟亡故,眉宇间有着股并不明显的阴翳和哀愁。
之后的破事天童觉没参与,也不想参与,只是他曾经抱胸看着坐在台阶上的牛岛,嘴角扯起稀奇古怪的弧度:“我觉得你这次不对哦,牛岛君——”
六月大赛的对手很难缠,及川彻带领的青叶城西也让白鸟泽尚未成形的队伍烦成了狗。他们聚精会神地对付这些人,繁忙的训练、合宿、练习赛,就这样到了高三的最后一年。
要回过头来了解她的过去甚至有些困难。
天童觉只知道实惨是实锤。
“紧张吗?”黑仪忽然问。
“诶——我吗?”天童指了指自己,他还以为她单纯在问牛岛,“我可是奇——迹——男——孩satori!”
黑仪怜惜了一下他的中二病和智障,伸手覆住他交握起的有些冰凉的双手:“进入白鸟泽的第一场比赛,多多少少会紧张点吧。”更何况是极力想要寻求自由自在打球的地方的天童觉,临时磨合的新队员和崭新的对手都会成为不小的压力点。
“奇迹男孩satori怎么这么像什么偶像男团的名字?”黑仪自言自语地吐槽,抬头看向天童,“手不仅冷还抖成这样,不紧张个鬼?”
“我没抖!”天童抽出手,伸出双手的食指对着黑仪,阴阳怪气地说,“害怕的是小——黑——仪你自己吧?”
她又不上场她怕什么?黑仪不想继续吐槽了,转而去珍惜时间地收拾放在板凳后的水杯。但她想了想,还是继续和天童搭话,“没什么好怕的,毕竟有觉的拦网在。”
他的拦网?
他……从小被人否定到大的拦网?
天童见黑仪拿着水杯直起身子,刘海阴影铺盖下的双眼亮得骇人:“为白鸟泽带来胜利吧,奇迹男孩。”
大概是队员的呼唤,天童看着她走远,那身穿紫白相间的强豪队服的背影同此刻,她有些拔高的背影重叠在一起,又和他记忆中走在前方的十六岁的月岛黑仪重合在一起。
她穿着那些看起来时髦俏丽的服装,削瘦的身形不能完全撑起衣料,在他眼前一晃一晃地挽住身边牛岛的手臂,转头冲他笑得皎洁无暇。
“白鸟泽不错吧?”
“跑起来的时候风吹在脸上,就能感觉自己和天空都融为一体了。”
“若利那玩意不太靠谱,你们能成为朋友真是太好了……啊怎么一副老妈子语气。”
“天童?河童?”
“觉,奇迹男孩satori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