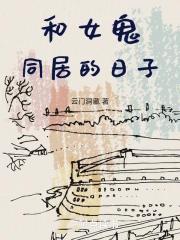泉州小说网>天宇开霁笔趣阁 > 第24节(第2页)
第24节(第2页)
如此亲密。他听说过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比如,亲手为?她簪钗,就算是情侣之间的嬉戏。他忽然笑了,抬起左手,揽着华瑶的后背,掌心透过轻薄的锦缎,依稀摸到她的骨形。她迟疑着伏进他的怀里,手指拉扯他的衣带把玩。
谢云潇的另一只手握着那支玉钗,在她发间稍微比划了两下,这才慢慢地把玉钗插了进去?。
华瑶依然坐在他的腿上,被他的手臂环抱着。他的衣袖沾尽了她的香气,怀中是温香软玉,指间是青丝缭绕,这般缠绵的情致对他来说却是难耐的折磨。高阳家的公?主惯会玩弄人心,他既想放开她,又想把她搂得更紧。
华瑶的神?情自然流露,原来是在观察他的喉结。
谢云潇抬起头:“喉骨有什么好看的。”
华瑶脱口而出:“因为?男女有别,所以我想知道什么是我有的,而你没有,或者你有的,我没有,我都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白。”
谢云潇从容不?迫道:“依你之言,你我私下相处时,倒也不?必藏私……”
谢云潇还没说完,华瑶就像是被诱饵吸引的一尾鱼,离他更近了。习武之人耳聪目明?,他能听见河浪击船的水声,她清浅的呼吸声,以及,接下来,她的指尖在他的脖颈处轻缓抚摸的几近于无?的声息。
他一把按住她的手:“行了,殿下,到此为?止。”
华瑶的嗓音很轻:“你怕什么?我根本没怎么碰你。”
说完,她起身离开,似乎连一丝留恋也无?。
*
掌灯时分,船上开宴,华瑶和谢云潇的属下们把酒言欢,闹作?一团。他们聚在一起玩起了牌局。依照京城的俗规,大家赌了一点小钱,每个人都是有输有赢。
燕雨输了两百枚铜币,心疼不?已,含恨道:“见鬼了!岂有此理,凉州人赌钱的本事还真不?小!”
齐风道:“不?是他们太强,是你太弱。”
燕雨恼羞成怒:“你胡说什么啊,我比你这种?从头到尾都没上过牌桌的人,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齐风冷冰冰道:“你要是输光了,别找我借钱。”
燕雨怒气更盛:“你也没多少?钱啊,你摆什么阔?”
夜间行船并未减慢,白帆高高地悬挂于桅杆之间,船头的风浪更大了。宽广的河道上浮起一重?又一重?的薄雾,船舱的灯火错落不?齐,全被遮掩在夜色与雾色的深浅不?一处。
幸好船工都是凉州本地人。他们在水上漂泊多年,无?须罗盘也认得路,船队又往前行了几里,齐风忽然说:“不?对。”
燕雨问:“哪里不?对?”
他们站在船尾,齐风举目远眺,眉头越皱越深:“有两艘船,跟了我们一整天。”
燕雨马上清醒过来:“我立刻去?禀报公?主。”
话音未落,远处飞射一道白色的信号烟,燕雨高声喊道:“急报!急报!全船备战!”
喊完这一嗓子,燕雨又喃喃自语:“完了,我不?会游泳。”
燕雨转过身,正好望见杜兰泽迎风而立。她的衣袖全被乱流吹开,露出纤弱瘦削的腕骨,他忙说:“你快跳船,乘小舟先跑,不?然真没救了,待会儿我们可?顾不?上你。”
杜兰泽却说:“等等。”
燕雨急忙道:“等什么!河上有水贼!”
二?人谈话间,那两艘贼船破开雾色,越来越近,从不?擅长水战的皇宫侍卫如临大敌。
贼船上黑压压一大片人,船头竖着两门?大炮,炮口粗约三尺。那水贼对官船势在必得,疾速追击,还有一名身穿银色盔甲的首领立在船头。
那水贼的首领年约二?十?来岁,身材颀长笔挺,容貌异常俊美,眉目暗含一股肃杀般的刚毅,兼有一身的豪迈英气。他腰间挂着一把沉重?的长刀,刀鞘在灯光照耀下闪着凛凛寒光。他大喊道:“请你们把谢云潇叫出来!”
燕雨万分惊恐道:“这贼人,竟然认识谢云潇!怕不?是来寻仇的。”
齐风没作?声,杜兰泽声嘶力竭地回话:“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那个水贼二?话不?说,直接跳下了船,踩着水面、顺着风浪奔向杜兰泽所在的官船。